目录
快速导航-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香樟树下的三家巷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香樟树下的三家巷
-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每滴血都有记忆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每滴血都有记忆
-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在寸土与海风之间:澳门的生态图谱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在寸土与海风之间:澳门的生态图谱
-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夜捕鱼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夜捕鱼
-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天地间的蝎子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天地间的蝎子
-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椒秀田垄
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学专辑 | 椒秀田垄
-
小说看场 | 幸运的男人
小说看场 | 幸运的男人
-
小说看场 | 树杈男孩
小说看场 | 树杈男孩
-
小说看场 | 鸽子飞吧
小说看场 | 鸽子飞吧
-
散文天下 | 沙漏的城市
散文天下 | 沙漏的城市
-
散文天下 | 山上的树和山下的院子
散文天下 | 山上的树和山下的院子
-
散文天下 | 诗歌主持人语
散文天下 | 诗歌主持人语
-
散文天下 | 在田野上(组诗)
散文天下 | 在田野上(组诗)
-
散文天下 | 玻璃海(组诗)
散文天下 | 玻璃海(组诗)
-
散文天下 | 诗一束
散文天下 | 诗一束
-
散文天下 | 减速黑鸫(组诗)
散文天下 | 减速黑鸫(组诗)
-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蒋述卓 唐诗人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蒋述卓 唐诗人
-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遥远的相似与自然的生长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遥远的相似与自然的生长
-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城市水文学:广州与卑尔根的城市文学掠影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城市水文学:广州与卑尔根的城市文学掠影
-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邵栋《不上锁的人》:山水有根,栖居有魂
“广州+”城市文学论坛 | 邵栋《不上锁的人》:山水有根,栖居有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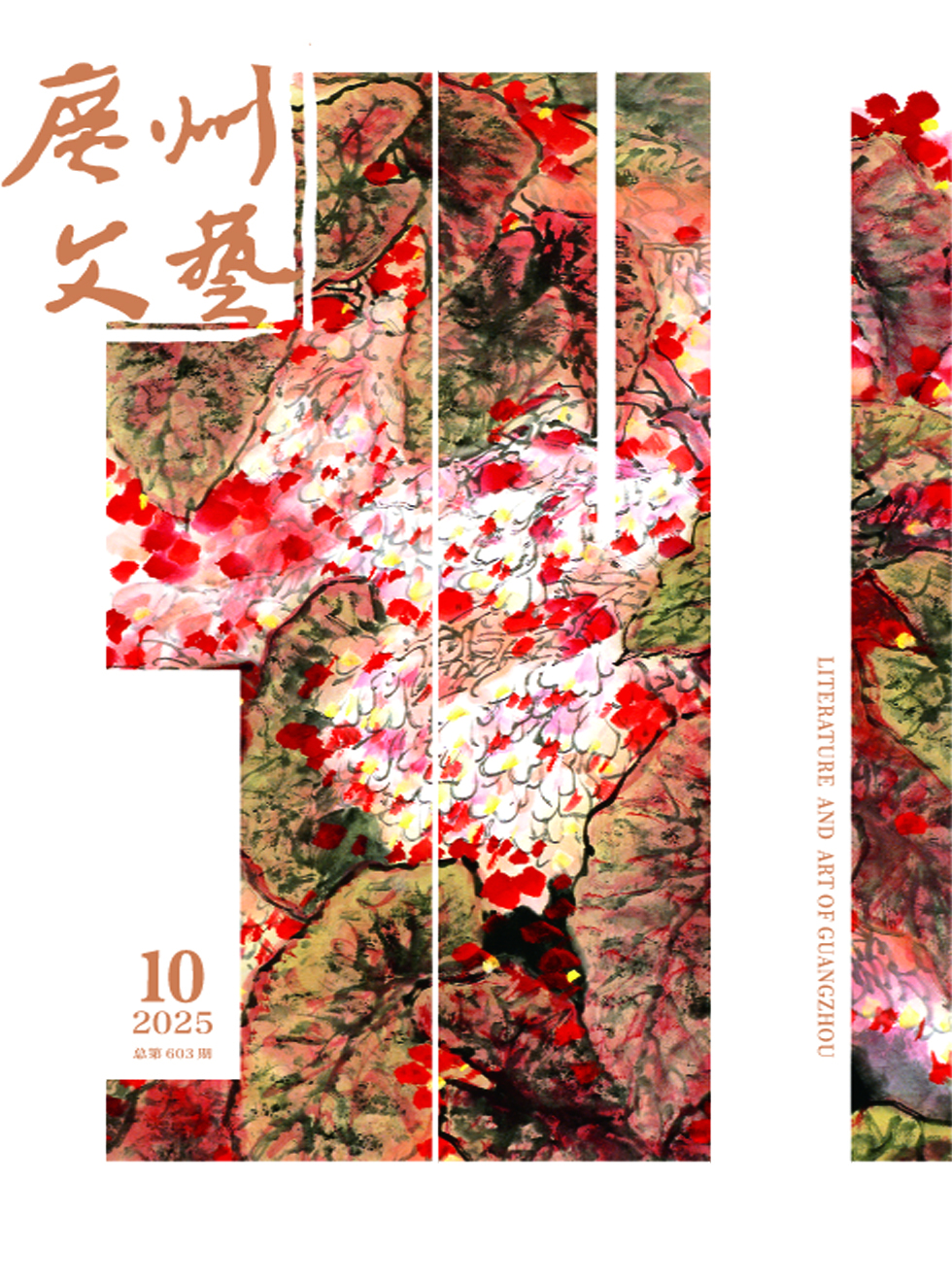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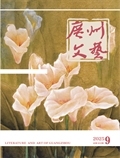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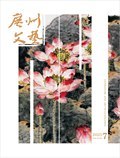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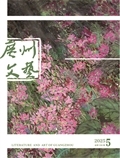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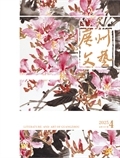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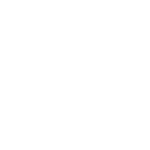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