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访谈 | 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与写作
访谈 | 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与写作
-
访谈 | 附录一 韩少功创作年表
访谈 | 附录一 韩少功创作年表
-
访谈 | 附录二 韩少功作品目录
访谈 | 附录二 韩少功作品目录
-
前沿·重述九十年代 | 新时代的中国“故事”
前沿·重述九十年代 | 新时代的中国“故事”
-
前沿·重述九十年代 | “狂飙”时代的罪与罚
前沿·重述九十年代 | “狂飙”时代的罪与罚
-
前沿·重述九十年代 | 市场经济改革初期的“江湖”世界与“完人”理想
前沿·重述九十年代 | 市场经济改革初期的“江湖”世界与“完人”理想
-
理论 | 新时代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与“新红色经典”
理论 | 新时代“人民史诗的文学”与“新红色经典”
-
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“数字北京”,何以言说?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“数字北京”,何以言说?
-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在今天回顾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出版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在今天回顾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出版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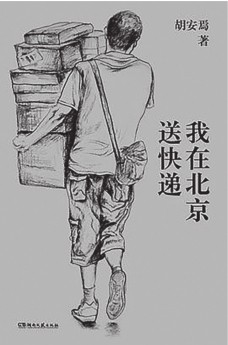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中为什么没有“北京”?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中为什么没有“北京”?
-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以“在场”写“真实”
北京来信·数字北京 | 以“在场”写“真实”
-
多维经典 | “勿以为问是虚幻”
多维经典 | “勿以为问是虚幻”
-
多维经典 | 穿行风暴,唱哀艳与晶莹的歌
多维经典 | 穿行风暴,唱哀艳与晶莹的歌
-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“文学之外”:文学与其他学科、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“文学之外”:文学与其他学科、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
-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“世界”从何而来?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“世界”从何而来?
-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科技的文学变奏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科技的文学变奏
-
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中国游戏,文脉待通
新学人·文学之外 | 中国游戏,文脉待通
-
作家批评 | 创意写作与“剩余的文学性”
作家批评 | 创意写作与“剩余的文学性”
-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山河铺满孔雀肺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山河铺满孔雀肺
-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《只此青绿》的媒介适应性:“翻译”与再现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《只此青绿》的媒介适应性:“翻译”与再现
-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青绿回响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青绿回响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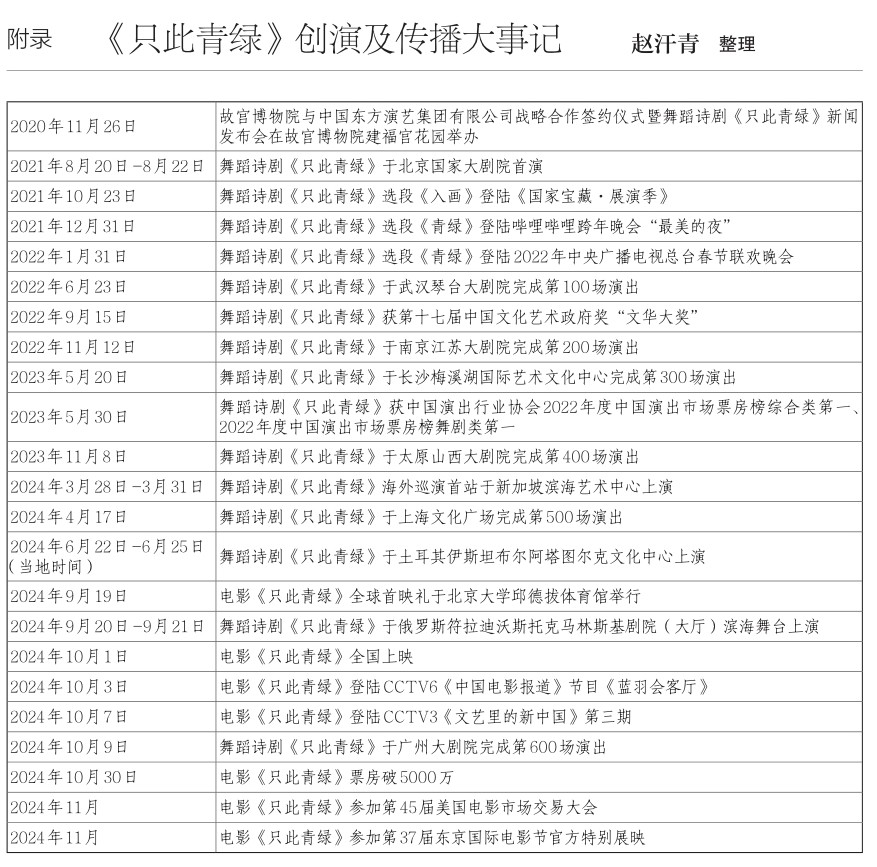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希孟教会了我“向死而舞”
文艺立交桥·《只此青绿》 | 希孟教会了我“向死而舞”
-
视界 | 硝烟与玫瑰:2024年俄罗斯文学观察
视界 | 硝烟与玫瑰:2024年俄罗斯文学观察
-
诗歌共时体·论焦虑 | 主持人语
诗歌共时体·论焦虑 | 主持人语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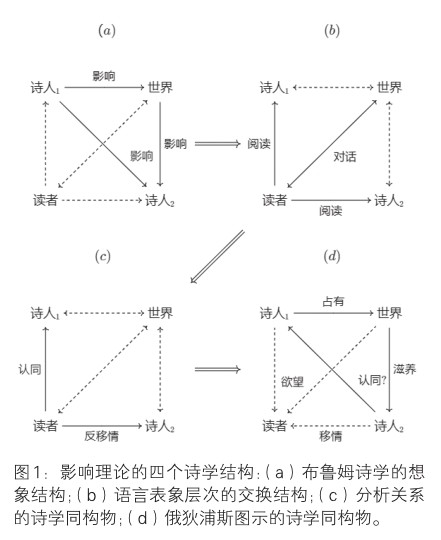
诗歌共时体·论焦虑 | 论焦虑,或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三个神话
诗歌共时体·论焦虑 | 论焦虑,或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三个神话
-

艺术场 | 在地与在场
艺术场 | 在地与在场
-

艺术场 | 不尽与未尽
艺术场 | 不尽与未尽
-

艺术场 | “连续的整体”
艺术场 | “连续的整体”
-

艺术场 | 艺术的有限或无限
艺术场 | 艺术的有限或无限
-

艺术场 | 艺术何以在地
艺术场 | 艺术何以在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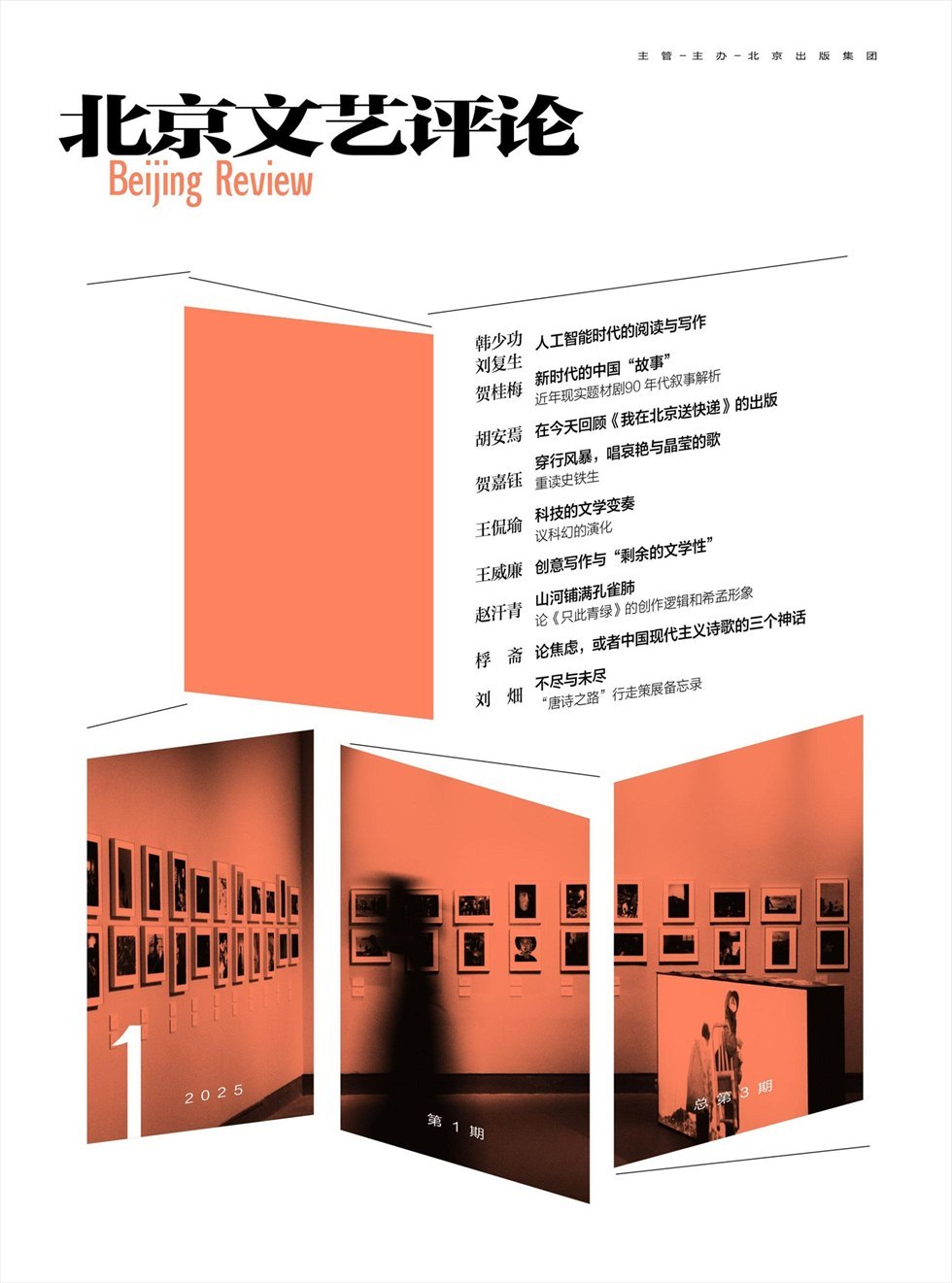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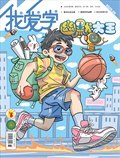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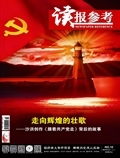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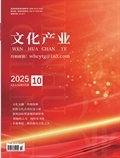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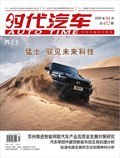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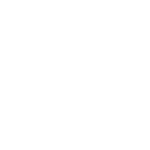
 登录
登录